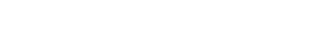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荷花奖比赛中,由新疆文联舞蹈家协会选送、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创作并演出的男子群舞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以98.5全场最高分折桂,这已经是新疆在中国这个最有影响力赛事中的三连冠了(2017年《长长的辫子》、2019年《花儿永远这样红》)。这一成绩对于中国任何一个省份、直辖市或者直属院团来说,恐怕都是一种“高度”乃至“高峰”。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、舞蹈评论家冯双白先生评价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:“取得了维吾尔民间舞蹈舞台艺术创作的重大历史性突破”,这其中意涵二层:维吾尔舞台艺术(创作)、重大历史性(突破),其核心关键词就在于“创作突破”。作为一位史学家,冯先生之观点无疑是一种基于历史纵线和共时生态的“判断”。而究竟是怎样的“目光”才能让我们更宏阔也更精准地意识到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的“重大”与“历史性”呢?
一、远看历史性“突破”
维吾尔族喜好歌舞、尤善作乐,早已为我们所熟知。强烈的地域辨识度、浓郁的艺术风格、多彩的民俗风情,这似乎已然是现代“维吾尔”舞蹈舞台艺术创作的审美范式,其固有的节奏型、传统的舞蹈姿态与步伐,符号化的服饰妆容,都成为了一种“典范”。但这种“范式”和“典范”在意味着“高度”同时,无疑也成为新时代维吾尔舞蹈创新性转化、创造性继承需要仰望的座座“高峰”。或许也正因为如此“高难”,才更显得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的“难得”。
可以说,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不仅是维吾尔舞蹈舞台艺术创作的重大历史突破,也是整个新疆乃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一个新节点。从选材上看,该作品聚焦于中国社会现实当下,且深刻而敏感地从新时代中国为实现美丽中国梦伟大事业,坚定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伟大梦想中,捕捉到“新疆麦盖提”当地民间艺人们在“气质”上发生的根性变化。
一亮相在舞台深处向着阳光引吭高歌的“麦盖提”,唤醒了呈一字排列坐着的“麦盖提们”,这群绿洲“巴郎”身着装饰着维吾尔典型“其娜瓦尔”图案的寻常白衫、黑裤、黑靴,个个神采飞扬,编导利用镜头变焦切换式手法,逐个表现了一个、两个、一群“麦盖提”巴郎的性格特征,令人惊艳的突破点就此出现:刀郎舞蹈语汇的打破与重组。只见在这群舞者们的肩部、脚下以及一致的呼吸顿挫之间,刀郎舞典型的节奏型被不断放大和强调,使其从听觉直接转换为典型的、可感的甚至是可触摸的视觉形象。更为关键的是这一“萃取”、“放大”、“重组”成为整个作品言语的发展逻辑,坐着的脚下、跪着的体态、移动的步伐、滚动的姿态、静止的舞姿,都不是传统中的“刀郎”,却又都是历史中的今天。这样的舞蹈语言设计,加上精致而严苛的训练,使得整个作品一扫“前文本”的熟悉,而呈现出“陌生”又有质量的艺术视觉。
于是,我们在中段看到当“麦盖提们”围成一圈,形成有中心表演空间的画面时,领舞者与一位衣着没有图案仅仅为普通白衬衣的“麦盖提”形成刀郎舞表演中规定程式:“对舞”。而精妙之处就在于领舞者是典型的“刀郎”而与其对舞的却是“鼓子秧歌”。两个形态与节奏都相去甚远的舞蹈语言,却被编导重组于新时代麦盖提的阳光下。在我们看来,这不是简单的“跨界混搭”,也非简单的“破壁出圈”,而是一种来自理性深处的“匠心”。若非编导在深扎采风里阅读到中央决定十九省市对口支援新疆,新疆麦盖提对应省市正是山东日照,那么今天阳光下麦盖提里也就不会有这神来之笔。但若没有极强的艺术直觉和创作技法,也难“玉汝于成”。所以,民族民间舞的创作,打破的前提是“深扎”,突破的基础是“热爱”,两相之间是舞蹈人直觉的理性:唯有“爱的深沉”“扎的深刻”才有我们“常含泪水”的感动。
二、近观气质性“守成”
我们应该看到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之“突破”,其实建立对刀郎舞乃至刀郎文化内在气质和情感机理的深刻把握上。今天我们谈论“守正创新”,或许也正是“念兹在兹”。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《刀郎木卡姆》是刀郎文化的“典范”之作,其每一套(曲)都有着“木凯迪满”、“且克脱曼”、“赛乃姆”、“赛勒凯斯”、“色利尔玛”五个部分。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艺术作品的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。有意思的是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也正暗合了这一结构。作品将其特有的节奏型与粗犷的“喉腔”唱法放大,变化其演唱速度、增加了音乐起伏变化的层次。这样选择,显然是编导围绕“舞蹈结构(形象)”展开的。
起势的向阳而歌,一字排列不断切换变焦的单一舞蹈动作与姿态,可看作“木凯迪满”(序曲),渐进的单纯的刀郎节奏、舞者们变换空间的典型舞姿,尤似“且克脱曼”的铺陈,逐渐进入刀郎对舞、舞者呈大方块横移,随后成漫天星似的典型刀郎舞姿主题舞段,以裂变重复形成限定空间中的丰富语言,恰似“赛乃姆”段的蓄势(叙事),而就在这时领舞者再次朝向正午阳光的引“喉”歌唱,似冲锋的号角、又似戏曲中的“紧拉慢唱”,随即“麦盖提们”以看似杂乱无章的圆形集中调度,重复着刀郎舞典型的舞姿步伐,将整个“麦盖提”推向高潮的“赛勒凯斯”段落,而其中不断跳出的幽默、吵闹、嬉笑、追逐的“麦盖提”形象,又让其多了一层“可阅读”的快感,及至最后舞者们在“高亢”的阳光中回到“色利尔玛”尾声。
需要再次提到该舞蹈作品中的服饰,它不仅跳脱了既有新疆舞蹈服饰艳丽的审美定势,同时也放弃了群舞舞蹈服饰色彩、式样多为统一的要求,而代之以整体“气质”相同,但杂有不同款式、样式、图案的妆容,这不仅成功地塑造了“鼓子秧歌”与“刀郎舞”对话形象,深化了作品反映生活、书写时代的现实主题,也再次奏响了新时代新疆各个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,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黄钟大吕。
著名舞蹈艺术家马跃先生在说起舞蹈作品《奔腾》的创作时坦言,在其中借鉴了很多其它民族民间舞蹈的语言特质。但他特别强调了在“奔腾”之前曾在内蒙古草原“深扎”两年的生活:“我深刻地了解这个民族的气质”。如此,我们再看《阳光下的麦盖提》,似乎也正是通过“深扎”的热爱、潜在的“结构”、萃取的“语言”、精妙的“包袱”,别具匠心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“那个”刀郎。
作者戴虎系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博士研究生,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
供稿: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